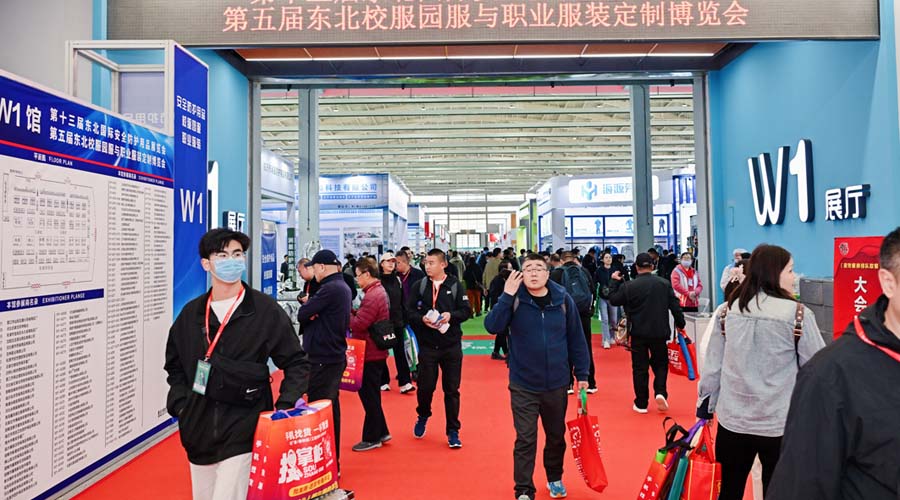穿过白纱手套和帆布手套的母爱
寒冷冬日,北风呼啸。搓着冰冷的双手,突然回想起小时候母亲给自己编织手套的情景。
小时候,在县城上学,最害怕的是呼呼啸叫的北风,那风像锋利的刀子,会在脸上、手上,割开一个个细小口子。我们当地人将那小口子,叫做“麻皱”,脸颊上,手背上,“麻皱”密密麻麻,纵横交错,像极了龟裂的老松树皮。
起初,为抵御风寒,我拎火盆去上学。但拎火盆的人多了,教室里经常浓烟滚滚漫,老师和同学被熏得泪眼婆娑,咳声不断,根本没办法进行正常上课,老师只好下达了“禁火盆令”。
火盆不准拎,怎么办?
母亲先是从建筑工地给我找来了一对帆布手套。帆布手套指头臃肿肥大,没有弹性,手指伸进去,空空荡荡,不灵活。记笔记、写作业,不摘手套的话字就写得歪歪扭扭。
母亲又想办法,从外面弄来了白纱手套。
白纱手套弹性十足,洁白有型,戴在手上,感觉比帆布手套强多了。那时候,谁能够戴上一对白纱手套,就会赢得大家的羡慕目光。
俗话说,有一利必有一弊。白纱手套漂亮灵活,熨帖,但一点不耐脏。戴在手上,就算特别小心翼翼,不去接触脏东西,但还是会留下黑印子。脏了,黑了,当然可以洗,只是,经过揉搓清洗的白纱手套已经无法回复先前的白净,并且还发黄,缩短尺寸,多洗几次,就不好用了。
母亲又在想办法。记得一个冬日的晚上,母亲坐在火炉边,从布袋子里拿出几团红、黑、蓝色的细毛线,然后叫我将已变形发暗的白纱手套摘下,细细比划来比划去。
母亲说:“别乱动,我给你织一双毛线手套。”
灯下,母亲全神贯注穿针引线。毛线断头了,她就细心结好线头,用剪刀轻轻修理那细小的须毛。随着母亲灵巧双手的不停穿梭,渐渐地,,我看到了指头的形状,手掌的形状。三色毛线,慢慢编织成漂亮厚实的手套。
呵欠连连的母亲,终于将一双柔软暖和的混色毛线手套戴在了我手上。比起白纱的厚实温暖,这毛线手套更柔韧,更有灵活度。
让我感到奇怪的是,母亲织的毛线手套,手指头处竟然没封口,戴在手上,除大拇指勉强被包裹完,其余四个指头和一个骨节都露在外头。
第二天,我戴着毛线手套去上学。开始感觉有些不习惯,总觉得露在外面的指尖有些冷。但慢慢我发现,不管是记笔记写字,还是上体育课做运动,甚至参加劳动,都可以戴着手套,因为它很温暖,很灵活。另外,比起白纱和帆布手套,毛线手套不易粘灰尘,特别耐脏。
这双温暖漂亮的杂色毛线手套,陪伴着我,安然度过了好几个寒冷冬季。
每到寒天冻地的时候,我总会回想起母亲曾经给我编织的那双露出指尖的毛线手套,想起母亲在火炉边编织手套时,专注、慈祥的样子。

版权声明:本文转载自网络媒体,仅代表作者观点, 与本网站无关。如资讯栏目文章和评论侵犯了您的合法权利, 请来电告知,我们将及时处理。